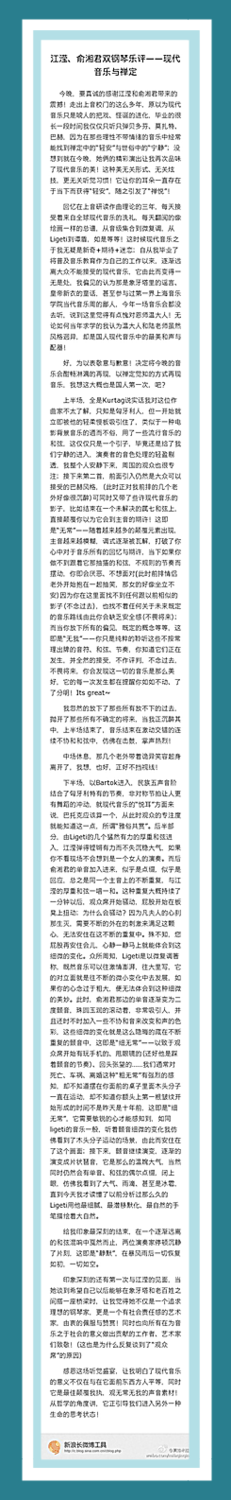“...das Zusammenspiel mit Chiang glänzte durch gegenseitiges aufeinander Hören, so dass eine ausgezeichnete kammermusikalische Teamleistung entstand. […] Das ließ Chiang etwas mehr Raum, ihr sensibles Klavierspiel zu entfalten, obwohl Herre stets genug Raum blieb, die musikalischen Vorzüge ihres Instrumentes zu präsentieren. Und das gelang ihr bei diesem Konzert überaus überzeugend.”
(Bonner Genaralanzeiger vom 26.7.2021 über das Konzert für Mandoline und Klavier)
“Ein großes Klang- und Kunstereignis gepaart mit einem außergewöhnlichen Können. […] Ganz hervorragend gespielt von Yin Chiang mit großem technischen und musikalischen Können sowie Hingabe! […] Huei Chiang konnte mit ihrer Violine durch die besondere Klanglichkeit und Virtuosität ihres Spiels, aber auch durch das fantastische Zusammenspiel mit ihrer Schwester Yin Chiang das Publikum mitreißen und sehr begeistern!”
(Gabriele Paqué über ein Konzert des Duo Sis in: Neue Musikzeitung Nr. 3/2018)
“Yin Chiangs Spiel zeichnet sich durch dasselbe Streben nach Perfektion aus, das auch ihren ehemaligen Lehrer Pierre-Laurent Aimard kennzeichnet […]. Ihr Anschlag ist klar, ihre Phrasierung transparent und doch erfüllt von einer Leidenschaft, die uns auf angemessene Weise den emotionalen Gehalt von C. P. E. Bachs Musik vor Augen führt.” (Hu Gengmin in: Nr. 107 / April 2016 der taiwanesischen Fachzeitschrift MUZIK)
“Von der Wiegenmusik [von Helmut Lachenmann], die Yin Chiang […] differenziert und kristallklar interpretierte, zeigte er [der Komponist] sich auf Anhieb begeistert […].” (Fabian Hemmelmann in: Zeitschrift der Musikhochschule Köln)
“Am Klavier erweist sich […] Yin Chiang als fabelhafte Partnerin. Sie hat Zimmermanns karge, dennoch dichte [Orchester-]Partitur, die auch religiöse Barockmusik zitiert, auf das Klavier reduziert. Sie verfremdet viele Töne oder zupft die Saiten harfenartig.” (Kölner Stadt-Anzeiger vom 5.3.2009 über die Premiere von Udo Zimmermanns Oper Weiße Rose in der Jungen Kammeroper Köln)
“[…] technisch makelloses Spiel, große Spielfreude und sehr harmonisch aufeinander abgestimmtes Agieren […]” (Mindener Tageblatt vom 13.6.2006 über ein Konzert des E. T. A. Hoffmann-Trios mit Nina Arnold, Rafael Caldentey Crego und Yin Chiang)
鋼琴家 江瀅 台灣古典音樂網專訪
訪問者:台灣古典音樂網專訪小組 (簡稱Q)
受訪者:鋼琴家 江瀅(簡稱 江)
曲目:布列茲 偶然發生的樂句
Q:您的經歷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新音樂方面,想請問:您在學習新音樂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過什麼困難?練習新音樂的作品和其他時代作品有什麼不同?演奏新音樂有沒有什麼訣竅?
江:其實所謂新音樂基本上是古典音樂發展的延伸,由於歷史是由後人給予過去的時間,根據其藝術文化風格下定義;而二十世紀的古典音樂,自從十二音列的發展,調式系統的解體,在人類還未能給予時代訂下名稱時,我們統稱之為新音樂。在練習方面,不論在音樂或技術方面遇到的困難,與在面對其他樂派作曲家的音樂時,是完全相同的。最大的不同是,這些新音樂都不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音樂,其他樂派的作品, 你可能在還沒練習時,已經聽過數千次了,耳朵及頭腦大概都知道最後曲子完成的風貌;但是練習新音樂,就像在走迷宮一般,你手上沒有地圖,所以得花較長的時 間,陪著曲子成長,給予它生命。唯一的優勢,是在音樂處理上的難題, 可以很快且直接地找到作曲家詢問,或是從其他與其工作過的演奏家中,取得間接的二手資料。
Q:您在廣泛接觸新音樂作曲家後,有沒有較偏愛的作曲家? (若現在還在世的)是否從這些作曲大師們學習或觀察到什麼,可分享給學習者嗎?
江:我特別喜歡 Luciano Berio (1925‐2003 義大利), Gyorgy Ligeti(1923‐2006 匈牙利), Gyorgy Kurtag(*1926 匈牙利)及Marco Stroppa (*1959 義大利) 的作品。 我從這些作曲家們的身上,看到他們對人性深刻情感的捕捉, 以及他們對待音樂時嚴肅與認真的態度。當然一位出色的藝術家,最重要的是要擁有無窮的想像及創造力, 以及其作品與自然和人類達到最美的協調。我覺得要在這制度化的功利現實主義中,依然能保持對音樂的執著與純真,應該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學習的方向。
Q:您曾在奧地利和德國學習, 帶給你什麼不同感受?
江:這兩個國家的學習情況完全不同。德國是個工業化國家,特別注重制度及效率。 一般人高中畢業後,就已準備職業導向,所以念大學並不是所有人的目標。他們的職校、專校、大學、音樂院及藝術學院都是同等的。在學習方面,教授期盼的是你主動求知,自己作學問,他們給予意見與方向,並尊重你的個人思想,把你當作成熟的音樂家看待。奧地利則是個非常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家,音樂院中強調的是德奧音樂傳統的延續,尤其正確音樂風格的養成,需要靠時間的洗練。這就是為何一般人在奧國求學,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尤其以東方人來說,要能深入西方文化的精髓,就如同毛毛蟲得經過結蛹的漫長時間,才能蛻變成美麗的蝴蝶。沒有經過這個過程,你的音樂語言是不標準純正的,像是帶有外國腔的中文。這情況若在英美, 會是一種個人特色,但在奧地利是不會被接受的。
Q:Pierre‐Laurent Aimard教授是德國推廣新音樂作品的巨頭之一,他個人有什麼特色?取得新音樂文憑的考試內容有?入學考較難還是畢業考?
江:Pierre‐Laurent Aimard 是我碰到在教學及演奏方面都極為聰明的音樂家, 我很幸運能在科隆音樂院與他學習,他的學生永遠維持在五人以內,完全因材施教。他可以很快的看到學生問題所在, 是位很有教學效率的老師, 他個人的博學多聞和豐富的人生閱歷,是讓我最為欽佩的一點。取得新音樂文憑的考試,就是整場現代音樂的音樂會。至於考試的難度,這是很主觀的問題,入學考要求的是一般古典的曲目及ㄧ首現代作品,至於個人音樂的造詣, 教授們很容易就能夠做出判斷。
Q:覺得歐洲的古典音樂市場仍然蓬勃嗎?
江:說實話,我覺得歐洲的古典音樂市場從來就沒有蓬勃過!古典音樂一直屬於社會歷史中的精英教育,它的市場永遠比不上流行音樂的市場,但是它是寫入文化歷史的。唯一和亞洲不同的是,歐洲人多半從小會學一些樂器,他們 的音樂教育十分普及,在文化課程中也佔很大的比例。不過,這畢竟是他們自己的文化, 我覺得也是蠻合理的。
Q:您在歐洲的哪個國家演奏新音樂作品時覺得比較能被接受,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經驗?
江:我個人因為是從古典音樂走入新音樂,我在思想上理解也接受新音樂,但是在美學觀點上仍趨近於古典,所以我在選曲上會特別考慮觀眾的成份。只要是好的演出, 一般觀眾都能接受,音樂畢竟是時間的藝術,你如何在兩小時內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取決於表演的藝術及演出的技術水準,至於是莫札特的音樂或是布列茲 (Pierre Boulez) 的音樂, 這並無太大差別。我個人印象最深的反倒是在中國演出新音樂的盛況,在武漢演出時,八百人的音樂廳竟然能座無虛席,讓我非常感動,新音樂在中國的發展值得我 們注意。
Q:會不會計畫在歐洲演奏(或推廣)台灣近代或當代音樂家的作品?
江:我已持續在歐洲的音樂會中穿插華人的當代作品。今年暑假, 我甚至大膽的在科隆室內歌劇院中,舉行一場東方現代音樂會, 曲目當然也包含了台灣作曲家的作品 (比如潘皇龍教授的作品),這對歐洲人來說,是個非常奇妙的聽覺經歷。
Q:您任職新音樂歌劇的藝術總監,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江:科隆室 內歌劇院相較於一般歌劇院,規模和場地都比較小,所以舉凡在科隆當地的演出都是以鋼琴代替整個管弦樂團。我的工作是負責新音樂歌劇的演出,必須指導所有歌手,並在演出時彈鋼琴總譜。基本上這完全是一位指揮的工作,也是許多指揮家想進大歌劇院的跳板。我是在2007年臨時代理一位指揮及作曲家, 在兩星期內負責所有的演出,因著當時的表現,使我獲得了為現代歌劇演出擔任音樂總監的機會,也讓我得到一般鋼琴家不會接觸到的範圍,學習到許多劇院的生態以及挑選訓練歌手的方法。
Q:您在台灣的音樂會中有演奏新音樂嗎?迴響如何?就你所知台灣目前的音樂環境有沒有人在做推廣新音樂這個部分?
江: 當然,我在台灣的音樂會,都耕耘於新音樂這塊土地上。我想對愛好音樂的知識分子來說,能現場聽到現代音樂史上作曲家的曲子, 應該是件令人興奮的事。在台灣一直有許多作曲家們,默默地在做推廣新音樂的事, 只是大眾在這商業利益導向的社會中, 很容易被淹沒而聽不見文化上發出的聲音。
Q:您在台灣想如何推廣新音樂?
江: 我覺得推廣新音樂最有成效的做法,就是辦音樂節與研習營。在歐洲已經有許多世界知名的新音樂節以及附屬的研習營, 例如 Klangspuren Festival (奧國音樂節), Lucerne Festival (瑞士音樂節), Acanthes Festival (法國音樂節), 以及 Darmstadt Ferienkurs (德國達姆城夏令營)等。這種集中式的做法,讓有興趣的人,可以很快且容易地找到學習與接觸的方向。至於這種方法是否能在台灣具體施行,我因為已離開這土地長達十六年之久, 無法作正確及客觀的市場評估與判斷。
2011 4月 德國